风声|调解结案的风险:转身撞人案反转背后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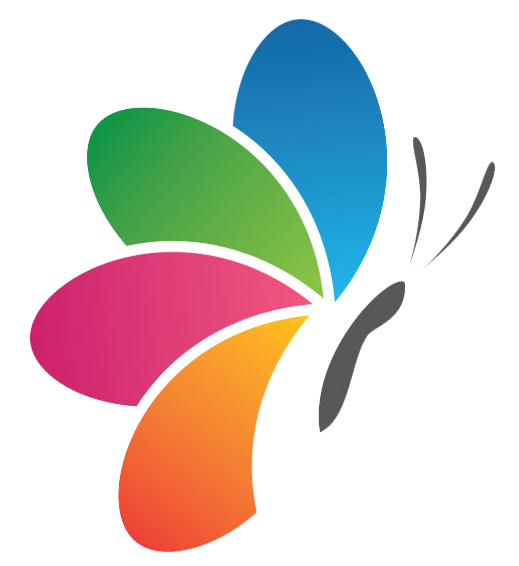 摘要:
作者|陈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近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的一起调解案例引发舆论关注。该事件最初因普法视频被公众知悉。原案情称,两人在人行道上前后同向而行,前人边走边...
摘要:
作者|陈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近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的一起调解案例引发舆论关注。该事件最初因普法视频被公众知悉。原案情称,两人在人行道上前后同向而行,前人边走边... 作者|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的一起调解案例引发舆论关注。该事件最初因普法视频被公众知悉。原案情称,两人在人行道上前后同向而行,前人边走边接听电话,其间突然转身往回走,而后人正常行走来不及躲闪,二人相撞造成前人骨折。经法院调解,后人同意赔偿部分医疗费7万元。法院就此向公众解释法理:前人无突发情况突然转身,对于相撞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后人未保持安全距离,承担次要责任。
这一解释,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首先,“安全距离”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第43条机动车安全距离的条款,认为行人未保持安全距离造成事故的,需承担责任。该条款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但是,法律对于行人之间的安全距离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可以把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类比为道路交通中车和车之间的互动,司法机关的解释过于牵强。
其次,行人在公共场所中应当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但在此案中的注意义务是否设置过高,从而导致赔偿分担过高呢?最后,本案中的受伤一方年龄大且伤情较重,法院是不是存在偏袒 “弱势群体”,优先考虑身份属性而扭曲了过错程度呢?
事情发酵几天之后,央视公布了此案的现场监控视频。视频显示两人确系同向而行,前人放慢脚步接电话并缓慢转身,而后人“东张西望,未注意前方”,对于相撞确有过错。法院承认“表述不当”,向公众道歉。
反转之前,有人将此案和彭宇案类比。2006年的彭宇案,曾经引起法学界和全社会的广泛争议。一审法官在认定相撞双方均无过错之后,根据公平责任分担损失,要求彭宇承担40%的赔偿责任。时至今日,对于该案中“是撞是扶”的事实真相仍有争议,但假如二人真的相撞,一人着急上车,一人着急下车,双方都存在视线盲区的情况下,法官认为均无过错的意见并无不妥。
不过,要在均无过错的情形下进行公平下判,并没有那么容易。彭宇案一审判决书直接给出了分配的结果,对于分配理由和衡平考量表述不足,被曝光之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正因如此,法律界一直都在反思:再遇到类似案件时能够有更为成熟的解决方案,应当如何行使裁判权,如何才能做到既专业又不违背朴素的法感?
青岛转身撞人案刚引发热议时,《法治理想国》的编辑问我怎么看。我反问:你呢?他告诉我:自从认识了我们这帮法律人之后,遇到这样的事都怕生错气表错态,毕竟还是专业意见为先。我听完忧喜参半,这是普法的好处,还是坏处呢?
一方面,人们更加趋于理性,因为互联网上的反转已不陌生。尤其涉及个案,在不能阅卷的情况下,案外人无法简单依据普法宣传的几句话进行评判,因为当事人陈述的细节和他们的态度,都会对法官判断造成影响。而这些,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另一方面,为何法律的专业性时常冒犯民众的朴素法感?从以往的经验看,法律的规则精细且例外多、解释多,而民众更乐于接受确定和唯一的结果,当看到明显不符合预期的结果时,就会觉得“不可捉摸”。而法律人也愿意说,这不是立法的错,而是司法的错。
也就是说,板子不应该打在法律身上,而是法官身上。但追根究底,法律本身是有限的,人类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它真的能搞清楚事情真相吗?真的能解决这样的大城小事吗?
这需要极高的司法智慧,我们把这样的期待交给了个案的法官,英美法系国家交给了陪审团。陪审团成员来自民众,以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对事实做出判断,将民意融入司法,也许更经得起社会的检验。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难以避免舆论、情感因素以及“从众心态”的影响。这也是全世界的法律圈一直面临的共同困惑。
回到本案,调解结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调解,一直是基层民庭结案的温和方式。在法院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对于双方争议不大或案情简单的案件,调解既节省时间,又不会剑拔弩张,再加上双方是自愿达成一致,执行起来也相对顺利。
作为律师,我经常跟当事人说,要边打边调,立案前可以调,审理过程中随时调,执行前也可以调,咱们不放弃任何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可能与很多人要求的黑白分明、对错泾渭并不吻合。
但,法律不仅追求公平正义,还追求效率和定分止争。公平正义要求严谨的程序和精准的裁判,这可能与追求效率所需要的快速处理之间,产生时间和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定分止争还要考虑社会和谐稳定,这也会带来公众对个案认知的困惑。
作为研究程序法的学者,我也更关注本案的程序选择。调解与判决相比,可以使法官回避做出困难的法律判断。程序会直接影响实体,因为审判要求法官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严格依照法律作出判决。而调解是当事人双方彼此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案件事实即使不清楚也并不会影响调解结果的合法性。在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很少申请再审,这就使得法官的“错判”大大降低,造成了法官逃避做出判决而以调解的方式结案。
程序的适用,也关系到权利属性。直接下判是适用审判权,而调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特别指出,“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这充分保障了当事人妥协的权利。
换句话说,为了解决问题,当事人可以“改写事实”,这是他的权利,他愿意吃点亏或者占点便宜都是法律允许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法官“能调则调,当判即判”。在调解程序中,不能为了回避矛盾而刻意为之,不能违反自愿原则,不能向当事人施加不当压力。同时,个案的调解方案,并不适合推导出适用于类似情境的普遍规则,譬如人人都要遵循行走的“安全距离”。这就违背了调解制度的初衷,也会影响公众的朴素判断。
因为,每个案件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当事人、法律关系和具体情境。调解方案往往是量身定制的,注重实际效果和双方的意愿;直接将其推广为普遍规则,既可能影响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又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以及道德的滑坡。这也正是我们还要对本案进行释法说理的原因。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 | 萧轶
作者:访客本文地址:https://www.ddwi.cn/ddwi/10814.html发布于 2025-05-12 15:27:58
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爱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