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昕孺:AI给诗歌带来的将是双重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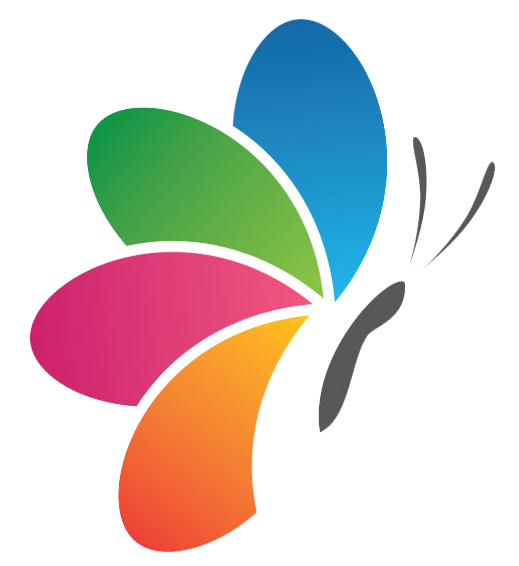 摘要:
【导言】每人一句诗,AI来组合。从2025年清明节以来,一种AI诗歌的全新玩法,率先从张家界“破圈”。由凤凰网和张家界大峡谷联合主办的“AI峡客吟——2025诗...
摘要:
【导言】每人一句诗,AI来组合。从2025年清明节以来,一种AI诗歌的全新玩法,率先从张家界“破圈”。由凤凰网和张家界大峡谷联合主办的“AI峡客吟——2025诗... 【导言】
每人一句诗,AI来组合。从2025年清明节以来,一种AI诗歌的全新玩法,率先从张家界“破圈”。由凤凰网和张家界大峡谷联合主办的“AI峡客吟——2025诗歌盲盒共创大赛”,一经推出,便迅速点燃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激情。而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内,每天成千上万中外游客,时不时驻足于大赛宣传物料前,举起手机扫码录诗句,情绪价值拉满。
事实上,“诗歌盲盒”的玩法,是用一种极简而有趣的方式,让所有人都能无门槛地参与诗歌创作,提升情绪表达的“高级感”。
这无异于一场全民文学实验。当AI与诗歌融合,曾经时热时冷的诗歌,会以什么姿势融入普罗大众的生活日常?新场景会不会催生新机会?
4月22日,在“华人国学大典乙巳春集”上,石厉、吴昕孺、余世存、杨雨、彭敏等知名诗人和文化学者现场集句,交给DeepSeek和豆包分别来组诗和二次创作。AI当场开出的“诗歌盲盒”,让在场观众见识了AI写诗的非凡功力。而由此引发的文学讨论,也如雪片越来越多。比如,AI真的可以完全成为人的“嘴替”吗? AI时代会不会掀起一场文学革命或者文艺复兴?当AI开足马力进行文学创作时,一切文学传统还有存在意义吗?“碳基人”干得过“硅基人”吗?
要想以“魔法”打败“魔法”,恐怕一切基于经验的发问,都将被颠覆;甚至,连问题可能都是多余。但我们仍有必要发问,有必要重新思考诗歌的存在价值,思考数千年或近百年来诗歌写作传统的演变历程。
那么,如何看待新旧之际的诗歌变革、传统与现代的困境、以及“碳基人”与“硅基人”的文学之战?“华人国学大典乙巳春集”活动期间,凤凰网特约撰稿人甘敏求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教育报刊集团总编辑吴昕孺进行了深度访谈。
【嘉宾】吴昕孺,本名吴新宇,湖南长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湖南省作协教师作家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湖南教育报刊集团总编辑。出版长篇小说《千年之痒》《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小说集《金黄的老虎》、随笔集《书中自有人如玉》、长诗《原野》等三十余部。【采访】甘敏求,资深媒体人,现居湖南长沙。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曾入展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获2021中国书法年展全国楷书展优秀奖、第五届林散之书法双年展优秀奖、湖南省第三届中青年书法大展优秀奖、“2018-2019长沙文艺新人”提名奖等。
以下为访谈实录整理:
壹|旧瓶新酒?诗歌创作的“变”与常
甘:华人国学大典总撰稿人柳理先生,与你是同乡、好友,你们也都是湖南师范大学的高材生。你喜欢写新诗,他沉迷于旧体诗,你们如何互相评价对方的诗?
吴:我和柳理是同乡,是好友,都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但他是中文系高材生,而我当年阴差阳错地到了政治系。所以在古典文学造诣上,我与柳兄有云泥之隔。我并不知道柳兄如何评价我写的现代诗,他对我写的长篇小说《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有过好评。我的诗歌,估计他看得不多,评价也就是“一般而已”。坦率地说,我是能接受这个评价的,因为我对自己诗歌的评价也是这四个字。
柳理,自号散人,我称之为“少壮鸿儒”。他的旧体诗,我认真读过一些,因对格律素无研究,所以不评判优劣,只讲一点:柳兄是我周围众多旧体诗作者中,绝无仅有的能给我带来古典文学营养的诗人。
不仅是他的诗,他的留言条、邀请函都很有味:“时维清和初夏,芳菲未歇;湘水衡云,嘉气徐开。诚宜青梅煮酒,品藻风流,击节砥砺,畅叙衷怀。当此暑期未暄、盛景盈庭之际,岳麓书院诚邀诸位良师嘉友……” 这是他发给我的于2015年5月28日在中国书院博物馆多功能报告厅举办“湖湘文化十杰评选高峰论坛”的邀请函。幸亏只是个邀请函,如果正儿八经作文,那《兰亭集序》就会紧张得冒汗了。
甘:在这个时代,写旧体诗是否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两千多年的诗歌史,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了,那些翻来覆去的意象也用烂了,给人陈旧之感,很难出新。旧瓶为何很难装新酒?
吴:任何一种创作都不能说“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哪怕像汉赋那样空洞无物、徒有其表的文体,现在也还有单位用来装裱门面。但毫无疑问,旧体诗的确是过时了,不然不会称之为“旧”。窃以为,旧瓶装不了新酒是很正常的事情,既然是新酒,就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新瓶来装。所以,诗从唐到宋就演变成词,到元又演变成曲。
很多诗歌爱好者包括不少写作者在内,满足于对古典诗歌的模拟与套写,陶醉于把诗歌写得文句优美、琅琅上口,对诗歌的现代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作品看上去很“美”,但因其直白的抒情、空洞的套话、陈旧的意象、单一的手法而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
甘:关于传统的问题,韦政通先生说,“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的进步抑或是退化,完全靠人自己。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传统,而在于没有把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你认为,写不好旧体诗,究竟是传统太桎梏,还是今人缺乏创造力?
吴:韦先生的话似是而非。首先,传统一定是出现问题了才会成为传统,这就像前浪一定是后浪把它拍在了沙滩上;其次,优秀的传统本身就具有创造力,它能从内部让自己通过革命而焕然一新,好比后浪其实就是前浪的一部分。
所以,“传统”和“创造力”无法分开来谈。所有古代诗歌文体在它们刚问世的时候,都是“新诗”;所有现代诗总有一天也会变成古体诗。从诗歌这个大家庭的角度来说,古诗和新诗不是断裂的,而是相互连接。传统蕴含着所有的现代性,而现代性必定是对传统的继承和扬弃。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学问不分古今中外,否则“新”就变成了与旧的对立。诗歌同样如此,新诗绝不是旧体诗的对立面,而是一脉相承。
现代人不写或写不好旧体诗,既不是传统太桎梏,也不是今人缺乏创造力,而是旧体诗这种表现方式早已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古体诗维度单一、格律严苛、容量有限,它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最适合变化缓慢的时代和环境。一旦社会变革加剧、都市文化发达、地域界限消失,特别是科技日新月异,让整个时代有如脱缰之马,每个人都陷入快节奏、高压力、强内卷而不能自拔,读点、写点古体诗或许有些抚慰作用,但无法解决我们内心深处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的灵魂焦虑与精神饥渴。
文学一定是时代的反映,一定是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升华,它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来。现代诗的产生,是远比古代复杂的现代社会和多维的现代生活,要求文学作品有更加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更为自由的表现形式。现代人的问题是现代性的,现代的文学便应运而生。
甘:你讲的这个很有道理。不过,写新诗必然要颠覆旧有的格律传统吗?中国诗词的形式与汉语本身的特点紧密相关。单音节,方块字,材料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最佳表现形式:格律诗。就如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材料是木材,决定了不以高度取胜,而以平面铺开的层层院落来体现人间秩序。不像西方建筑的石头材质,可用来盖高耸入云的教堂,将人引向天国。
中国诗词确实适合写韵文,自带一种音乐性的美。叶嘉莹先生说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是“循着声音去找字”。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写作技巧,擅长在易感的语言形式上制造种种效果。
所以,有许多人认为新诗割裂了古典语言及文化传统。你认为这种割裂是否违背了汉语言本身的特点和优势?
吴:汉字的象形、表意和形声使之具有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它自有一种不可复制的优雅风范,除了你上面说的音乐性,她还有画面感,有的汉字本身就蕴含着诗意。
这么好的材料,足够文脉的传承和文体的发展,根本不是“格律诗”所束缚得了的。无论经历多大的祸乱,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学三千年来从没断裂过,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母语的无穷韧性与魅力。
上面说过,新诗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旧体诗“油尽灯枯”之后的自我革命与脱胎换骨,它不仅没有割裂中国的古典语言及文化传统,没有违背汉语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反而在西方现代诗的参照下,更能发挥汉语富有音乐性、画面感,音形意相结合等独特优势。
甘:但从新诗的历史来看,没有产生伟大诗人,也未能建立自己的传统。
吴:个人认为,假以时日,中国新诗的成就将毫不亚于旧体诗。新诗自1917年诞生到现在才108年,已经涌现出很多优秀乃至杰出诗人。至于“没有产生伟大诗人”,和时运也有很大关系。这一百来年的前六十年,家国忧患,有产生伟大诗人的社会条件,但那时中国新诗实在太过稚嫩,挑不起这副担子;后五十年,新诗创作水平突飞猛进,却已进入治平之世,“国家不幸诗家幸”,反之亦然。在技巧上或已炉火纯青的当代诗人,大多衣足饭饱、养尊处优,缺乏突破某种时代局限和社会规范的风骨与笔力,要出现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谈何容易。
我们要认识到,一种文体的繁盛固然需要伟大的创作者来支撑,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认知度与民众的接受度。中国新诗虽然存在不少争议,但已完全融入当代社会生活,融入当代人的情绪建设和情感表达中。可以说,她正在建立自己的传统。
闻一多先生诗才不俗,他的新诗作品并没有完全从古体格律中挣脱出来,他在新诗创作过程中产生迷茫和挫败感,从而发出要“勒马回缰作旧诗”的感叹,是十分自然的。饶是如此,闻一多一生也只写了46首旧体诗,新诗却有100多首;他广为流传的作品没有一首旧体诗,而是《死水》《七子之歌》等新诗作品。
我再强调一下:传统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中国新诗就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诗歌传统不断创新的产物,她与诗经、离骚、古诗十九首、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脉相承。
吴昕孺参加由凤凰网、张家界大峡谷联袂举办的“华人国学大典乙巳春集”。
贰|传统与现代:最大困境在哪里?
甘:复古看不到出路,但写新诗似乎也没有形成共识。当代写诗如何摆脱这两方面的困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最大困境在哪里?
吴:说新诗没有形成共识,我觉得至少是欠准确。我们谁没有读过新诗,谁没有自己喜欢的现当代诗人?有的人喜欢徐志摩,有的人喜欢穆旦;有的人喜欢余光中,有的人喜欢洛夫;有的人喜欢海子,有的人喜欢北岛;有的人喜欢余秀华,有的人喜欢刘年……
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上千人齐声朗诵北岛《回答》的场面,那不是共识吗?余秀华一本诗集能销几十万册,这不是共识吗?如果连起码的共识都没有,新诗如何能取代绵延两千多年的古体诗,难道是靠政府的一纸红头文件?如果连起码的共识都没有,朦胧诗潮如何能在改革开放之初推动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难道是靠某个英雄人物的振臂一呼?
不要怀疑新诗,真的。新诗已经很棒了,有很多优秀作品和优秀诗人。汉语的优化与活化不能没有新诗,否则就会有固化与僵化的危险。至于有关新诗标准的争议,公说公好,婆说婆好,那有什么关系,历朝历代不都是这样的吗?
被誉为“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为什么被称为“古诗”,还不是在当时不受待见,它的价值是被后世评论家和读者挖掘出来的。《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在他那个年代也不是以大诗人,而是以大隐者闻名,如果没有白居易、苏东坡等“铁粉”的极力推崇,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很可能就被绑定在“二流诗人”的位置上。
任何写作都有困境,任何写作都是面临困境的写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困境就没有写作。所以,写作要摆脱困境是伪命题。就像一山望得那山高,写作就是跨过和迎接一个又一个困境。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最大的困境在哪里?个人认为,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传统中肯定有不少落伍的、需要我们汰洗的东西,也肯定有很多优良的、需要我们传承的东西——这个课题每一个现当代诗人都无法回避,我们得去甄别,去选择,再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
为什么文学艺术倡导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要不断通过陌生化形式教导人们学会看,因为世界每天都是新的,而我们往往熟视无睹,用旧眼光看世界,你会觉得世界就那样,都是旧的。
确认世界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我认为,这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头。
甘:许倬云先生说,“当代文化的新观念,是以自然流露代替规律,以认识主观代替假想的客观,以多元代替一元独尊。这些文化的展现,可能缺少优雅,可能喧哗浮浅,却是比较真实自然也有尝试的勇气。”
然而,这种表层多元的背后,却面临结构性的趋同。当代流行书风便是如此,看多了,表面千变万化,骨子里却是一致的。你认为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
吴:许倬云先生这段话,呈现了文化“现代性”的诸多特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以人为本,以人性代替物性。人的自然流露,人的主观内心,人的思想多元,代替了物性的规律、客观(何况还是假想的)与一元独尊。
表层多元背后的结构性趋同,也印证了许先生所说的“这些文化的展现,可能缺少优雅,可能喧哗浮浅”,但许先生认为,这没有关系,它们都是“比较真实自然也有尝试的勇气”。
我认为,结构性趋同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某种新思潮、新理念带来的群体创作,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潮引发的校园诗歌创作热,那个时候的校园诗歌巨多而且同质,但由于有许先生所说的“比较真实自然也有尝试的勇气”,所以无伤大雅,而且是中国现代诗取得突破的必由之径。
另一种结构性趋同就是盲目跟风,只有模仿没有创造。书法都摹兰亭集序,诗歌都学苏东坡,这当然不是好现象,但也无须过于在意。书法家哪能个个都是王羲之,诗人哪能个个都是苏东坡!正如《红楼梦》可以养活成千上万个红学家,如果兰亭集序、东坡诗能让成千上万模仿者过上好日子,那也是一桩功德啊。唯其如此,我们才更能体会到王羲之、苏东坡这些富有原创力的书法家、诗人的伟大。
更何况,结构性趋同现象对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者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优秀读者必须去培养自己发现美、发现“金子”的眼力与见识,优秀作者则不得不加强自己的原创力与辨识度,从而在结构性趋同的天罗地网中脱颖而出。我们要相信读者,相信时间,“泥沙”绝对留不下来。
叁|未来,人写得过AI吗?
甘:这次在华人国学大典乙巳春集上,你谈到AI写诗带来的影响,长远来看持悲观态度,认为未来“碳基人写不过硅基人”。但书法界一直很乐观,认为书法永远不会被AI取代。你为何不像书法家那样乐观?
吴:人工智能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冲击是革命性的。书法界的乐观自有其道理,我不作评判。我还是来说说诗歌。
AI给诗歌带来的将是双重革命。
第一重在当下。AI的出现将诗歌创作的门槛大大降低,几乎是没有门槛了,每个人输入关键词都能通过AI写出诗来。现在,至少六成以上的人类写作者写不过AI——这些人要不不写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将转化为AI写作者,看上去AI只是工具,但仅输入关键词全部由AI写出来的作品能算是人类的作品吗?
有人说,由AI写出来,人类再修改不行吗?为此,我只能付之一笑:你都要AI来写作了,还能改得比AI写的更好?那么剩下的少部分人类写作者,三四成或者二三成——这些人要不不写了,(我希望)更大的可能是,AI逼得他们写出原创性更强、辨识度更高、更富有热血和思想的作品,逼迫他们殚精竭虑,一步步登峰造极,这些人很可能将成为固守人类原创写作的殉道者。
第二重在未来。就当下而言,AI对诗歌创作的挑战,我还是比较乐观的。AI才刚刚开始,各方面都很稚嫩,仅有大数据一项绝对优势,其他与人类比尚不如小儿。因此,目前AI创作出来的作品意象繁复、“金句”堆砌、风格单一,过于周密……一句话:数据味浓而人情味少。
所以我们发现,当下AI最擅长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古体诗,特别是对联和赋。也就是说,那些不需要投入多少情感、更接近文字游戏的作品,AI靠强大的数据系统和整合能力现在就能打败人类。
然而,要呈现人性的幽微复杂与命运的深妙莫测,每一个文学作品不仅要有细节,还要有细节中的细节,不仅要有情感,还要有情感中的情感……这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东西,就不是现在的AI能够表现得出来的。我想,这也是乐天派的理由所在吧。
我认为,乐天派只看到了当下,他们认定AI只是一堆机械构件,按钮由人来操控,没有自己的意志和灵魂。大家想想,碳基人不也只有一堆肉质构件吗?拆分来看,肝是肝,肾是肾,“意志”在哪里?“灵魂”在哪里?都没有。我们的意志和灵魂,我们的精气神,都是在血、肉、骨与五脏六腑有机结合之后,生发和激发出来的,它们都不是实体。
那问题来了,随着AI不断发展升级,它们以晶片为细胞,以部件为骨架,以电流为血脉,以模型为大脑,以各系统为脏腑……久而久之,它们难道不会生发情感和意志,从而产生精神和灵魂吗?
所以,我对未来是悲观的,我觉得总有那么一天,碳基人会写不过硅基人。而且,这种落伍将是全方位的,对人类的精神成长而言,也可能是毁灭性的。
作者:访客本文地址:https://www.ddwi.cn/ddwi/9102.html发布于 2025-04-29 10:02:05
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爱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