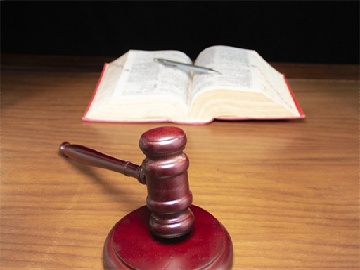比较法视角下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立法完善与配套机制构建
本文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立法完善与配套机制构建,通过对现有制度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改进建议,旨在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的立法规定,并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保障人权,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摘要:比较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自由刑停止执行制度会发现,域外对有精神病及其他严重疾病、怀孕、哺乳、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形,不宜在监所内服刑的罪犯,允许其在监所外就医、分娩、哺乳或被照料,相应时间不应计入刑期,这与我国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计入刑期的做法不同。域外停止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精神和宪法原则中保障服刑犯的基本权;但监外治疗、分娩、哺乳期间的处遇毕竟不同于刑罚,时间过长会不成比例地影响刑罚执行效果和刑罚目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故应按下“暂停键”,不将监外时间计入刑期。借鉴域外做法,权衡基本权保障与刑罚目的实现两项利益,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改宜将暂予监外执行改造为自由刑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同时,为了抑制部分罪犯试图获得无限期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的投机心理,须从完善审批流程管控,健全具保制度,严密收监条件以及加强监狱医院建设等方面做好配套衔接机制建设。
关键词:暂予监外执行;暂缓执行;停止执行;基本权保障;刑罚目的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于被判处监禁刑,但因有严重疾病、怀孕或哺乳婴儿等情形不适合在监狱等执行场所内执行刑罚的罪犯,暂时采用不予关押,将其安置在监所外交由社区矫正机构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变通方式。
暂予监外执行仍然是对刑罚的执行,虽具有暂时性,属非常规执行方式,但执行期间仍要计入刑期,效力与收监执行相同。不同的是,暂予监外执行的场所在“监外”,与监(所)内执行的强制性和管控程度有明显差别。立法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网开一面,给予特殊照顾,让他们回家在社区中生活或者接受治疗,社区中舒适的环境和较好的条件更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疾病治疗”。由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人身自由未被剥夺,在公共医院治疗和家中生活,与监内服刑形成巨大反差,导致实践中一些服刑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伪造病情诊断或检查证明文件,虚构保外就医条件,获得暂予监外执行。如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通过贿赂看守所所长、医生等人,以虚假的疾病诊断证明获准保外就医,法院宣判之日即被暂予监外执行,从法院直接回家,从此泡茶楼、开宝马、住高档小区。直到2011年,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林崇中被违法暂予监外执行一案立案侦查,林崇中才被收监。再如,广东省电白高考舞弊案主犯陈建明被判有期徒刑8年,在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情况下“越狱”成功,长达8年之久。还如,内蒙古巴图孟和故意杀人后“纸面服刑”15年,一天刑期未服便从看守所取得了释放通知书,后又摇身变“村官”,蒙混入党,当选旗人大代表,后因贪污罪再次锒铛入狱。
众所周知,执行刑罚一方面具有教育改造功能,通过服刑让罪犯认罪悔罪,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后能够走向正途,避免再犯;另一方面具有抚慰功能,通过服刑让罪犯认罪服法、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安抚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情绪,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然而,违规暂予监外执行,不仅助长了罪犯的投机心理,不利于其接受教育改造、悔罪自新,还会让被害方心绪难平、难获慰藉,甚至会第二次被害,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本应在监所服刑改造的罪犯,仅因一纸保外就医的虚假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就堂而皇之地“逍遥狱外”,享受各种人生红利,这是对司法公信力的严重损害,更是对法治的极大破坏。
基于对违法暂予监外执行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近年来,国家在多个方面从严整治暂予监外执行中“提钱出狱”“纸面服刑”等突出问题。在规范层面,《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严格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范围、审批及取消程序:建立暂予监外执行的负面清单,对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规范保外就医的证明条件,规定保外就医的证明文件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在诊断的基础上开具;完善外部监督机制,规定检察院对暂予监外执行有权开展事中和事后的同步监督;明确违法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后果,规定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及时收监,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对违规暂予监外执行的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401条还规定构成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犯罪。在实践层面,法院、检察院及司法行政系统自上而下开展了各种查处违法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专项活动。2021年开展的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就将违规违法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作为六大顽瘴痼疾之一集中整治。“在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全国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办理的1524万件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开展全面排查,对‘踩点减刑’‘立功减刑’等160余万件重点案件进行评查,核实认定问题案件8.7万件,其中减刑问题4.6万件、假释问题7890件、暂予监外执行问题3.3万件”。
然而从近年来的刑事执行情况看,“顶风作案”者有之,违法暂予监外执行亦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实践中,“有的罪犯本来已经病情明显好转,无需再保外就医,但为了应付病情核查,故意临时大剂量服用与治疗效果相反的药物;有的罪犯身体本身并没有严重疾病,为获取医院的严重疾病诊断证明书,竟然采取顶替调包等手段;有的女性罪犯此次哺乳期还未满,便又故意再次怀孕,甚至持续怀孕分娩达四五次之多,这样近十年的时间便过去了……”该类案件的共同特点,主要是罪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未被交付执行前或者在执行刑罚后不久就被暂予监外执行,造成刑罚全部或大部分都是在纸面上“服刑”完毕。而上述事件的发生,几乎都与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间可以折抵刑期这一“制度缺口”相关。不容否认,暂予监外执行允许罪犯离开监所却又不停止刑罚执行,这对任何罪犯的诱惑力都是巨大的,这样危险的“激励”使部分罪犯千方百计地利用暂予监外执行的机会逃脱监禁刑的制裁。有人大代表提出,治本之道是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改为“暂停刑罚执行制度”或“暂缓执行制度”。“保外就医制度存在缺陷,把暂予监外执行的时间计入了刑罚执行期。国外类似的制度都是保外就医的期限不计入服刑期,这样就使很多暂予监外执行和保外就医的罪犯失去钻法律空子的动力”。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计入刑期这一问题切入,借助比较法的研究方法重点剖析暂予监外执行及相应期间应否计入刑期的理论基础、底层逻辑,进而论证暂予监外执行向刑罚暂缓和中止执行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从技术层面探究暂予监外执行改造为刑罚暂缓和中止执行后,监外长时间的疾病治疗、康复等是否依然会有潜在的负面激励,如果有,相应的规范约束机制是什么?这些讨论将为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刑罚暂缓执行和中止执行制度及其配套衔接机制提供理论建言,希冀为当下暂予监外执行中“提钱出狱”与“纸面服刑”等沉疴痼疾开出药方,做出理论贡献。
二、域外停止执行制度的规范梳理
违法暂予监外执行屡禁不止的原因可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罪犯在监外执行比收监执行所受处遇差别明显;二是因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计入刑期,若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能拖至刑期届满,便可彻底逃避监禁刑。“贪腐官员们绝大多数人其实一天牢都不想坐,但因为受到对于减刑、假释二者适用中最终实际执行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期一半的规定的限制,在这两个环节动‘提钱出狱’的脑筋,不是最优的选择”。可见,暂予监外执行一定程度上甚至比适用减刑或假释的法律效果还要优越,这也是不少服刑犯中的投机者青睐暂予监外执行的重要原因。
比较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制度可以发现,域外对于罪犯身患精神疾病及其他严重疾病,或有怀孕、哺乳、生活不能自理等情形不宜在监所内服刑的,一般都会中断或暂停刑罚执行,允许罪犯在监所外就医、分娩、哺乳或被照料,监外期间大都不计入执行刑期,这被称为自由刑停止执行制度,与我国的立法例有明显差异。
(一)德国自由刑停止执行制度
在德国,自由刑的执行会面临各种障碍,当刑罚执行无法开展或继续便会出现执行停滞(Strafausstand)现象。依执行障碍出现的时间节点不同,执行停滞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刑罚执行开始前有法定事由须停止行刑,称为暂缓执行(Strafaufschub),也称为刑罚的推迟执行,法定事由如患病、身体状况或监所的设施不适宜立即执行等;另一种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也就是执行开始后停止行刑,称为停止执行(Strafunterbrechung)。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5款中的交付执行前和交付执行后的暂予监外执行不同,在德国无论是刑罚执行前的暂缓执行,还是执行过程中的停止执行,相应期间都不计入刑期。
以德国的停止执行为例,在该国刑罚实践中,适用停止执行制度意味着自由刑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障碍,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正常执行,需要暂时中断刑期的计算。德国围绕刑罚执行有较为全面细致的立法,在联邦层面有《德国刑事诉讼法》《德国刑事执行法》以及《德国刑事执行规则》等,在各个联邦州还分别制定有相应的《刑事执行法》。从内容上看,与停止执行制度有关的规范条文主要包含两类:一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55条第4款、第455a条和第461条,二是《德国刑事执行规则》第45条、第46条和第46a条。《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55条第4款和第455a条分别规定了停止执行的两类实体性事由,前者是以受有罪判决人的疾病为由,后者是以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为由,但无论何种事由,停止执行的期间都不会折抵刑期。不同于前两个条文,第461条规定了服刑犯住院期间刑期的折抵,效果上更类似于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
1.因受有罪判决人的疾病而导致的自由刑停止执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55条包括对自由刑的暂缓执行与停止执行,第4款规定了因受有罪判决人的疾病而导致的自由刑停止执行,“(四)如果有下列情形,且预计病情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执行机关可以停止执行自由刑:①受有罪判决人患上精神病,②因疾病,执行可能危及受有罪判决人生命之虞,或者③受有罪判决人身患重病,且在监狱或监狱医院不能查明或治疗。若有优势的理由与此相抵触,特别是公共安全理由,则不得停止执行。”该款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句,规定了受有罪判决人的疾病三种情形,第二部分是第二句但书条款。首先,从整体上看,对三种法定情形的认定需要作实质解释,受有罪判决人的疾病必须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一解释主要是从比例原则的角度区分本条与第461条的适用。若是病情持续时间较短,单纯监外执行便已足够,只有在病情持续时间无法确定或与剩余刑期“不成比例”的情况下,方可停止执行自由刑。那么,何谓“不成比例”?法律层面并未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多结合个案具体判断。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也发展出一些容易操作的标准,如超过自由刑刑期的一半等。其次,就具体内容看,对三种情形中的特定问题需作进一步的解释学分析。情形一的精神疾病,必须在刑罚执行之后产生或被首次发现,可以是偶发性的,但必须实质影响到判决的执行。情形二中因刑罚执行而危及生命的疾病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要求对被执行人本身具有紧迫的生命危险,且必须不受被执行人的控制;二是生命危险的出现与刑罚的执行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情形三相当于是前两种情形的兜底性条款,要求被执行人患有其他在监狱或监狱医院中无法查明或治疗的严重疾病。最后,该款第二句还规定了停止执行的除外情形。若是被执行人存在再次犯罪、逃跑的风险,基于公共安全方面的原因将会被排除停止执行的适用。
2.执行机构原因导致的自由刑停止执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55a条规定了出于执行机构原因而暂缓或停止执行刑罚的情形,“(一)如果出于执行机构组织原因需要暂缓或停止执行自由刑或剥夺自由的矫正及保安处分,且无优势的公共安全理由与暂缓或停止执行相抵触,执行机关可以暂缓执行,或者不经被押人同意停止执行。(二)不能及时取得执行机关的处置时,监狱长可以在第一款的前提条件下,不经被押人同意,暂时停止执行直至裁决作出。”相较于第455条,该条在实践中的适用率较低。从文义解释出发,适用第455a条第1款需要满足两点要求:一是因执行机构的原因导致停止执行具有必要性,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监所条件无法满足人道主义需求,如出现监狱满员或需要腾出合理空间给重刑犯等情形;二是不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此外,本条第2款还赋予了监狱长暂时性停止执行的权力,这主要适用于无法及时获得执行机关裁决的紧急情形。
3.特殊的监外执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61条规定了住院期间的刑期折抵,“(一)如果受有罪判决之人并非故意为中止刑罚执行而患病,刑罚执行开始后因病被送入独立于监狱的医疗机构,在该医疗机构停留期间应当折抵刑期。(二)在故意情形中,检察院应当取得法院的裁定。”同样是针对受有罪判决人患病的情形,但本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停止执行,而是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监外执行,监外执行期间可以折抵刑期。这种情形可简单理解为服刑犯因患疾病而住院的短期时间可折抵刑期。
(二)日本刑罚执行停止制度
日本刑事诉讼中与暂予监外执行类似的制度是刑罚执行停止,具体又分为必要的执行停止和任意的执行停止两类。
必要的执行停止是指自由刑的服刑者处于无责任能力的状态,根据检察官的指挥,在恢复正常状态以前必须停止执行自由刑。《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80条规定:“被判处惩役、禁锢或者拘留的罪犯处于心神丧失状态时,依据判处刑罚法院同级的检察厅所属检察官,或者罪犯所在地的地方检察厅所属检察官的命令,停止执行直至其状态恢复。”
任意的执行停止规定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82条,是指考虑到被判处自由刑的人的身体状况(健康、年龄、分娩前后的情况等)和个人、家庭情况等,由检察官裁量停止执行。
无论是必要的执行停止还是任意的执行停止,都只是刑罚执行的中止或者暂停,并不是监外执行刑罚。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81条的规定,检察官必须采取刑罚执行停止的事后措施,例如将犯人移交给负有监督保护义务者、地方公共团体的长官,使其收容在医院或其他适当的场所。服刑者在被决定停止执行刑罚前,留置于刑事设施内的时间计入刑期,其余时间则不计入刑期。因此,当刑罚执行停止的事由消失后,罪犯应当被收监继续执行自由刑。
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在70岁以上”的任意的执行停止事由属于不可恢复事由。在日本司法实践中,如果符合该情形的被执行人在起诉阶段未被检察官作出起诉犹豫处理,裁判阶段未被判处缓刑,通常不会停止执行刑罚。
(三)我国台湾地区停止执行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467条规定了自由刑之停止执行制度。第467条规定:“受徒刑或拘役之谕知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依检察官之指挥,于其痊愈或该事故消灭前,停止执行:一、心神丧失者。二、怀胎五月以上者。三、生产未满二月者。四、现罹疾病,恐因执行而不能保其生命者。”
我国台湾地区自由刑之停止执行与中国大陆的暂予监外执行有相似的适用情形,不同点是,自由刑之停止执行的时间原则上不计入刑期。这一点在我国台湾地区“监狱行刑法”第58条中有明确规定,“Ⅰ受刑人现罹疾病,在监内不能为适当之医治者,得斟酌情形,报请监督机关许可保外医治或移送病监或医院。Ⅱ监狱长官认为有紧急情形时,得先为前项处分,再行报请监督机关核准。Ⅲ保外医治期间,不算入刑期之内。但移送病监或医院者,视为在监执行。……Ⅷ衰老或身心障碍不能自理生活及怀胎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满二月者,得准用第一项及第三项至前项之规定。”据此,罪犯服刑期间如果患有疾病,在监狱内不能适当医治,需要保外医治或移送病监或医院,这其中的保外医治期间不算入刑期之内,但移送病监或医院的(我国台湾地区称“戒护外医”)则视为在监执行,要计入刑期。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对此作出解释(院解字第3788号):受刑人保外医治期间不算入刑期之内,“监狱行刑法”第59条第3项(现为第58条第3项)既定有明文,则从该法公布施行之日起(1947年6月10日起实施)自应一律遵办,院字第87号解释已因该法施行而不适用。
(四)小结
通过梳理域外刑罚停止执行制度会发现,其与我国大陆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有两点不同。
一是适用条件不同。依《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有三种适用情形:患病、怀孕或哺乳、生活不能自理,并不考虑服刑人的年龄、家庭结构、亲属情况等。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则更细致化地规定了刑罚执行停止各种情形,除了身患严重疾病不能在监所内继续服刑的,罪犯家庭困难、精神状况不佳、年老以及监所的设施不符合监禁条件等执行机构的原因都可以作为刑罚停止执行的条件。
二是性质不同。我国暂予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变通方式,虽改变了刑罚的执行场所,但仍是行刑方式的一种,并未停止执行刑罚,所以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计入刑期。而德日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罚停止执行只是在刑罚执行出现障碍时作出的一种应急处理,类似于审判中的中止审理,是对刑罚执行的暂停或中止,待暂停或中止执行的法定情形消失后再将罪犯重新收监执行剩余刑罚,所以停止执行刑罚的时间不计入刑期。这是两项制度的本质区别。
三、域外停止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仍是在执行刑罚,但域外的停止执行则是暂停或中止执行刑罚,故监外时间是否计入刑期有所不同。然而,停止执行与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形颇为相似,为何我国允许罪犯在监所外继续服刑,域外则采取执行暂停或中止的制度设计,背后支撑这一做法的法理基础、底层逻辑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德国的“一次性终结”原则
就立法变迁而言,德国刑事程序中的执行停滞最初只包含暂缓执行制度,规定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55条第1款至第3款,“(一)如果受有罪判决人患上精神病,应当暂缓执行自由刑。(二)受有罪判决人患有其他疾病,如果执行可能有危及其生命之虞,则适用前款规定。(三)如果受有罪判决人身体状况不适宜在监狱设施内立即执行,亦可暂缓执行刑罚。”直到1986年,《德国刑事诉讼法》才引入停止执行制度,规定于第455条第4款。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转变,主要取决于刑事执行基本原理的限制。德国法认为,刑事执行的价值在于“一次性终结”,即对刑罚的执行原则上应当一次性完成,不得中断。这不仅基于有效执行刑罚的公共利益需要,更是对被执行人权益的重要保障。据此,刑罚执行前遇有法定事由不能执行刑罚的,可以依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55条第1款至第3款先暂缓执行,从而保证后续一旦可以执行刑罚就能够“一次性终结”。
刑事执行的“一次性终结”原则类似于审判中的集中审理原则,强调庭审的不间断、一气呵成。不过,同审判中会出现被告人患病、逃跑等突发情况一样,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受有罪判决人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突发精神病及其他严重疾病等情形,导致无法在监所继续服刑。基于《德国宪法》第2条对人身权利的保障,受有罪判决人可以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61条在执行场所之外的医疗机构接受短期的治疗,并不会影响刑罚的继续执行。对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作出的判例中认可了宪法性基本权利和刑罚执行“一次终结”原则的兼容性,但同时增加了一项限制条件,“对人身权利的保护需求不能完全取代刑罚执行”。换言之,若是监外执行持续至刑罚执行完结,将会导致刑罚目的落空,那么刑期折抵将不再具有正当性。《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55条第4款的停止执行正是为解决这一困境而被引入,虽然突破了“一次性终结”原则的要求,但借助宪法基本权利保障与刑罚执行目的实现可以作出正当化论证。在保障宪法基本权利和实现刑罚执行目的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一次性终结”原则应作出妥协调整,设置必要例外,从而对受有罪判决人的刑期执行利益进行必要干预。
引入停止执行制度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多重价值的冲突与权衡,故在适用上须遵循比例原则。“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61条的规定,开始执行刑罚后,有罪被告人因病被送入与监狱隔离的监狱医院的期间,应当计入刑期。若其为了中断刑罚的执行有意患病则不可折抵,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应取得法院的裁判。若估计至有罪被告人再次适合执行(Vollzug)之时,其会在执行监狱外度过刑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则可以中断”。《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61条是计入刑期的停止执行,但只限于短期的抢救治疗,是对刑罚执行“一次终结”原则的坚守。第455条第4款则是不计入刑期的停止执行,适用于长期或无法预见期限终了的医疗救治。可以说,第45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