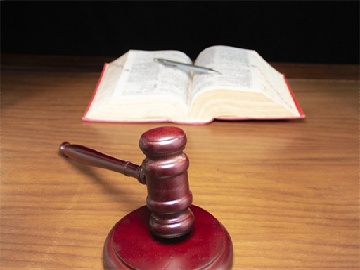律师视角下的民法典体系化实践思考
本文从律师的视角出发,对民法典体系化实践进行深入思考,探讨律师在民法典体系化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分析律师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民法典,以实现法律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本文还关注民法典体系化实践中的难点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以期为律师实务操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大家办案或者说分析案件,都需要体系化思考。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立法工作,《民法典》编纂最基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这种体系化的努力,实际上法学界到目前讲得比较少,研究得比较少。从律师业务的角度学习和研究民法典体系,是我今天报告的主题词。
一、近现代民法体系化立法的实践经验
事实上人类社会早先已经有了立法体系化的努力。不管中国古代的铸刑鼎、唐律,一直到清朝《大清律例》等等,实际上都是想把法律要法典化。法典化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消除法律的碎片,打造法律适用的体系化思维。适用法律分析案件的时候,得知道这个案件应该依据法律中哪一个部分去处理,而且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应该,知道这种案件跟别的案件的区分;你所依据的法律,它所渗透的法理和其他案件分析裁判所渗透的法理的区分。区分是法学的硬道理,也是它的最基本的道理。这就是体系化思维的基础。
近现代民法法典化的典型是首先是《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是做得最成功的一个楷模。《法国民法典》为什么要变成做法典?是因为伏尔泰启蒙思想的体现。伏尔泰在英国考察工业革命以后回到法国,在法国一个港口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说,这个演说被作为是法国启蒙运动非常重要的演说之一。这个演说中他提到,法国50多个省,其中涉及到民法的体系有2400多个,相当于一个乡镇就有一个乡镇自己的习惯法体系。在这个乡镇订立的合同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可能就得不到承认。那个时候没有汽车,人们出行都是骑马、换马。伏尔泰说我骑马从巴黎到外省去,马还没有换,法律就已经换了好几个体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换法快于换马”的传说。
伏尔泰说,像这种法律碎片分崩离析,非常不统一,就造成了人们对交易的恐怖,人们没有办法把制造出来的商品卖到其他的地方去。英国把商品卖到了全世界,可是法国的商品只能在乡镇上卖,这就是法律不统一造成的重大问题。这种说法后来对拿破仑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拿破仑下令尽快制定民法典。制定《法国民法典》的时候,拿破仑是一个34岁的军人。这么一个年轻的军人怎么能够编纂出来后世称为伟大的《民法典》?而且这个《民法典》还要以拿破仑来命名?原因很简单,就是拿破仑受到了伏尔泰启蒙思想强烈的影响。而启蒙思想中一个思想,就是要促进法律的统一。当然,他还受到了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革命的其他观念的影响,比如要落实人人平等的观念,落实私有权和所有权充分承认和保护的观念,落实意思自治的观念,落实法律上的平等责任,也就是过错责任,而不是身份责任的理念等等。法律从体系上统一,从思想上统一,这是拿破仑追求的一个很大的目标。
拿破仑在法兰西执政以后,就下令编纂《民法典》。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找来的学者和教授们,你争我吵的吵了三个多月,莫衷一是。拿破仑说从现在开始,《民法典》的国民会议由我来主持。他主持了57次《民法典》的会议,事实上《民法典》编纂的主要会议是由他主持的。在他的强力督促下,《民法典》顺利编纂出来了。就是因为拿破仑对这个法典的编纂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的议会曾经两次命名《法国民法典》为《拿破仑民法典》。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法律规范十分庞大的民法,被编纂为法典,这是启蒙思想运动的成果之一。《拿破仑民法典》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体系化。但是实现体系化更深层目标的,也就是最讲究体系化逻辑的,还是《德国民法典》。相比而言,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人是高喊理想的人,而德国人是脚踏实地的人。德国立法者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罗马法》以来的民法基本的规范构成,然后总结出来,从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五个要素的逻辑,以此建构《民法典》体系的逻辑,编纂出来了自己的《民法典》。
这两个法典,尤其是《法国民法典》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化效应。首先是欧洲大陆、然后是全世界非英国殖民地的国家,都开始编纂民法典,从而在世界上形成了民法法典化的运动。从欧洲兴起编纂《民法典》,才有了我们都知道的欧洲大陆法系,也叫民法法系,也叫私法法系。这个法系的法技术,不论是立法还是适用法律,和英国的体系不一样。大陆法系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民法典的效果怎样?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民法法典化,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这种追求立法体系化做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效果,叫做体系化效应。我的研究认为,体系化效应实际上有三大效应。首先一个是立法上的效应,一个是执法上的效应,一个是司法上的效应。体系化解决了习惯法背景下的立法碎片化问题。比如伏尔泰批评的法国民法的情形,一个国家有2400多个民法体系,立法都是碎片化的。这种情况,造成立法、执法和司法上的一系列缺陷。人们在用法律的时候不知道用哪一个。适用的结果很可能导致裁判尺度不一致。法律统一以后,立法首先统一起来了,执法的时候依据也是统一了,司法裁判的时候,法律也就统一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立法的普及效应。当时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德国学者讲到,为什么要编一个很大的法典,而且这个法典还要适合装在口袋里头?就是它要把法律交给普通大众去使用,普通大众出去经商或者做事的时候,口袋里都揣一个《民法典》,如果遇到了事情以后,他自己可以很方便的把法典翻开看看,看看自己的权利在哪里。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所以法典的政治效应也是很强烈的。
法典的编纂还有一个强烈的社会效应,就是体现了形式理性原则。大陆法系立法表面上都是冷冰冰的老百姓不明就里的法律条文,不像英美判例法那样有人有事,比如说克莱默诉史密斯,通过具体的案件总结法律规则。有人说,判例法上可以看出来法律到具体人身上的温情。可是大陆法系是具体的条文,没有任何活生生的人,也没有活生生的案例,只是说主体客体权利义务责任,看起来是冷冰冰的,没有温情。但是大陆法系的立法,冷冰冰的法条中实际上渗透了一种高度的理性和另一种温情。这个理性就是不能相信具体的法官,不能相信具体的官员,不能让法官和官员因人而异地裁判和执法,从而实现法律公平。民法法典化,就是要人们遵守法律,而不能看脸。这种法律的形式理性,通过条文的格式化,渗透了人文、对普通民众切实关切的另一种温情。
二、中国《民法典》确立的体系化思维
法典编纂实际上是很大的工程。尤其是民法典的编纂,涉及法律规范体量极大。不仅欧洲、法国德国有这个问题,在咱们国家也是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民法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就是法律碎片化。《民法通则》制定的时候,确定的立法原则叫做宜粗不宜细,宜短不宜长,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本着这个原则,《民法通则》当时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才只有156条。后来陆陆续续制定了很多单行法、特别法。但是,改革开放国家法律事务发展很快,立法来不及,最高法院就通过司法解释完善法律,其实就是司法立法。这种司法解释也不是体系化而是碎片化,一事一议。《民法典》生效的时候,最高法院废止的司法解释就有250多个,保持不废止的尚不知道有多少。最值得注意的是学者研究成果也都是碎片化的,针对一个问题做一个研究,所以没有形成很好的体系化思考的传统。这种学术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工作者。这就是我国《民法典》编纂时期遇到的大问题。
这种碎片化的法律助长了法律的执行和实施中的盲动。多少年来我们国家的行政执法问题是很大的,经常侵犯老百姓的权利。法院也有问题,一些法官是谨小慎微,一些法官是胆大妄为。案子办得实在不行,还说是因为从法律上找不到根据。以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即法律不健全,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通过法典的编纂,把改造社会的思想统一起来。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立法的统一。体系化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就要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不管是立法者也罢,法律的执行机构也罢,司法机构也罢,还有律师,都要养成系统化思维的传统。十多年来,我参加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工作,在全国人大立法活动中所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体系化科学化。我不赞成以前那样部门立法的思路,国家的立法不能只是体现部门立法的想法。部门立法只能解决部门自己的事情,不考虑整个法律体系本身,这就是典型的非体系化思维,这是不对的。但是几十年了,形成这个传统,纠正起来比较难。
体系化的思考,对律师业务的开展十分重要。我虽然没有做过律师,但是做仲裁员时间比较长,所以跟律师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发现,律师中间很多人也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思考。这可能是老师教的,因为大学老师多数都是在碎片化的法律培养中间成长起来的。一个老师给你讲一段,最后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很少有这种体系化的思考。所以我在这里不批评律师,而是批评律师的老师,就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人。碎片化的法学教育造成很多人分析案件很片面。所以现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再强调要避免机械式司法,我对此表示赞成。这个要求对律师也一样管用。
要建立民法的体系化,首先要明确民法立法体系这个概念。在我国我们要知道,《民法典》实际上不是全部的民事法律体系的法典。《民法典》实际上只是民法中间的普通法,《民法典》这个立法形式之外,还有民法特别法。这样我们就要考虑到,民法大体系中间的一般法和特别法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要掌握一般法和特别法的思考模式。在《民法典》中间的一般法规定了民法上的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和责任一般的情形。特别法可能大家平时不熟悉这个概念,但是其内容大家都是知道的。民法特别法有三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商事法律,以《公司法》、《票据法》所代表的商事法群体。最近全国人大也正在修订《破产法》,已经审议了两次。国务院提请一次,这次全国人大又审议,要推进《破产法》,目前属于商事立法的范畴。民法大体系中第二个大的特别法群体就是知识产权立法。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本身包含的内容很多,没有办法纳入到《民法典》之中。立法者对此的处理方式是,把它们都是规定在《民法典》之外,做一个特别法的群体来对待。《民法典》之外的第三个大的法律群体就是特别民事权利的立法。这个立法群体非常大。《民法典》128条规定涉及到老人、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消费者等特别民事权利的立法,也都是民法特别法的构成部分。实际上,我国最重要的特别民事权利立法是劳动者立法。特别民事权利最重要的是劳动者的权利,这也是非常重大的政治权利。目前这一群体立法被大家称为社会立法。但是,社会立法基本的原由还是民事权利。因为权利保障也都要落实到特别的自然人身上,落实到这些特别主体的民事权利之上。法律的展开、权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济,首先还是要依靠民法。比如劳动争议就是这样。所以在民法上是属于特别立法,这一部分法律也是非常之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立法必须要得到强化。
总之,掌握大民法体系,首先要考虑特别法和普通法之间的体系连接。在《民法典》编纂的时候,商法学会部分学者提出,《民法典》的编纂没有考虑到商事立法的需要。对此我提出了“头等舱”理论:《民法典》编纂没有规定商事立法的大量内容,并不是不承认商事立法在民法大体系中的地位,而是要把大量的商事立法内容作为特别法来考虑。《民法典》只规定商事立法的一般问题,而更多的商事立法的特殊性问题,交给《公司法》《票据法》等商事立法处理。而且在法律适用上,要充分考虑到商法的特殊性和商法的优先性。在法律适用上,商法坐的是头等舱,民法坐的是经济舱。在法律适用之时,商事立法是应该优先得到适用的,知识产权也是这样,特殊民事权利也是这样。但是必须记住一个道理,就是特别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清晰的时候,还要返还到适用《民法典》上来。头等舱理论,解决了一般法和特别法之间的立法和法律适用问题。
大民法体系思维建立后,就要思考《民法典》本身的体系逻辑。《民法典》本身的体系区分为总则和分则,总则反映民法的一般逻辑,像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和责任,分则是包括具体的权利规定。分则的区分逻辑,首先是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区分,财产权中间区分为物权和债权,知识产权大体上也有这样的规定。人身权是婚姻家庭中的人身权和人格权,大体上有这样一个区分。更细节的逻辑性的问题,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关于怎么认识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也有一些细节性的考虑,还有书和文章,大家有时间再看。
三、律师实践必须掌握体系化思考
从律师实践的角度看,法典总则和分则的区分逻辑,这是民法体系化最重要的分析和裁判的基础。我们一定要知道,总则是民法上的纲要和基础,体现了民法的基本思想。分则是不能违背总则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国《民法典》编纂是分为两步走的,先编总则,后编分则。在民法分则编制时,法学界出现了大量的违背《民法典》总则编基本思想的立法和学术观点。到现在也有很多人都还在坚持这样一些违背法典总则的观点。比如《民法典》109条规定了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这是人的基本权利。因为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这是人基本权利,所以它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自然人自己本身专有,只能他自己享有的。这是民法总则确定的民法基本原则。可是,也许有些律师朋友已经看到了,民法典分则编纂时,中国法学界出现了所谓人格权转让、甚至人格权商品化的观点。想一想就知道这个观点是很不妥当的。人格权自产生以来,就是自然人自己专有的权利,是为了保护自然人人格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把人格权转让出去,那他自己的人格依据什么来支撑呢?既然人格以及人格权都是专有的,那么怎么能转让给别人呢?怎么能进行商品化开发呢?想起来都是很可怕的。但是要知道这是中国民法学家提出来的。我国《民法典》编纂时期,我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些观点我坚决反对,最后这些观点没有被法律采纳。希望大家知道,人格权问题,涉及从古代奴隶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伦理分析,从民法伦理的角度看,人格权更不能转让,更不能商品化开发。因为时间问题,我今天跟大家讲实践性的题目,这个涉及民法历史的纯粹理论性的话题和大家的期待有点距离,我就不在这里深入介绍了。
从律师的法律学习和适用的角度看,我们一定要掌握和运用。总则部分的规定所发挥的四个大作用。一个是民法思维的底线作用,要在法律案件的分析和裁判过程中间,怎么分析都不能超越民法的底线,像《民法典》第一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立法基本的根据,从第3-12条规定的基本原则,这是法律的底线,是不能违背的,不能破坏的。实践当中有人身权的契约,涉及到人的性、婚姻等,违背了民法底线和人格尊严的,就是违背社会主义最基本价值目标的,就不会得到法律的成人和保护,反而还可能收到制裁。此外,总则对分则发挥的其他三大作用,即制约作用、解释作用、漏洞弥补作用,这些都是律师业务中经常应用的。
我讲一个总则对分则发挥制约作用的例子,比如说法律行为的分析。我们知道,《民法典》民事权利一章,规定的财产权区分为物权、债权等等。所以,在法律学习和实践中我们必须分清,在财产权里面有些是合同的债权,有些是属于物权性质的支配权。债权是请求权,物权只是支配权,这是两个大的不同类型的权利。在适用法律行为的法律规定时,我们就要明白,一个法律行为在涉及到民事权利变动的时候,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有些法律行为只能发生请求权的结果,而不能自然而然地发生物权或者其他支配权的结果。也就是因为这样,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主体的效果意思,在这里自然而然就区分开了。所以,当律师的,不能像有些老师理解的,认为现实的法律交易中就只有一个意思表示,只认一个债权合同。这个思维模式有点太简单了。这种思维,就像农贸市场的农民交易一样,两毛钱一根黄瓜,合同都是这样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必须知道,在市场体制下,尤其是在远期合同远程合同的情况下,必须区分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及其所产生的债权法的后果,和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所发生的物权上的后果的区分。因为合同的成立到合同的履行,是要隔一段时间的。合同订立的时候,可能合同上的意思表示是正常的,这些合同是应该得到承认和保护的。但是到履行的时候,因为时间过了一段,当事人的主观条件、合同履行的客观条件都发生变化了,合同履行就做不出来了。这时候,那就得分析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合同履行不能。这里的知识,也就是大家说的合同履行障碍的学问。履行遇到障碍的时候就仔细分析合同履行不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原因分析,得出一个妥当的结果。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修订我国的《海商法》。海商贸易中的交付,其方式非常多,所体现的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极其复杂,有债权意义上的交付,也有物权意义上的交付,还有纯粹移转占有意义的交付。如果你只是知道两毛钱买一个黄瓜,那你就根本无法理解海商法上的这些交付,更是处理不了这种交易上的法律问题。
有些大学老师到现在还在讲,因为合同必须要履行,因此就不应该把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区分开来,作为两个法律事实。他们认为法律交易就是一个法律行为,就是两毛钱一根黄瓜。甚至教育部主导的民法教科书也是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实在是太不了解现代法律关系学说,以及现代法律实践了。合同应该履行是对的,但是并不是生效的合同都能够得到实践上的履行,就是因为合同成立和合同履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这是必须区分开来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合同的履行不是自然的,而是由合同主体也就是当事人的意思推动的。这一点,构成了现代民法的物权变动理论和规则。限于时间,我今天不再多讲,请大家看看我写的《中国物权法总论》这本书以及我关于区分原则的一些著述就可以了。
此外,就合同成立和履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有很多法律问题需要研究。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合同履行不能的论文,对解读《民法典》第580条的规定做出讨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第580条规定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合同履行不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德国非常著名的法学家萨维尼,《德国民法典》就是按照萨维尼学术逻辑编纂成功的(当然这个法典不是他自己编的,而是他的学生温德沙伊德主持编纂的)。萨维尼曾经就讲到一个典型的合同履行不能的例子。他说一个老人跟别人订立了一个出卖住房的合同。订立合同的时候,这个老人当然是正常的,合同约定半年之后交付房屋。可是不幸的出卖人,到合同订立后第三个月的时候精神失常了。这样合同就遇到了履行不能的问题。他自己履行不了,法院也不能强制他去履行。因为,任何机关都不能要求精神病人去交付他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合同处于不能履行的状态。而且应该注意到的是,这种情况下,是没有谁违约的,买受人和出卖人都不存在违约的情形。我国《民法典》第580条规定的履行不能,其基础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在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况下,合同应该终止。这时候,其实主要是要通过买受人的努力,要使合同予以终止。买受人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因为合同订立的是有效的,买受人可能支付了定金或者其他费用。合同终止时,买受人需要通过法院把这些钱要回来,而且这些是可以要回来的。
这个典型的案子说明,现实生活中,一些没有得到履行的合同,并没有违约的问题。我国《民法典》第580条,条文立法的宗旨就是在合同当事人并没有违约,不能从违约角度下去考虑合同的终止问题。但是问题来了。在立法的时候,几位著名的民法学家就主张说,这个条文是“违约方解除权”的规定。最高法院的后来的司法解释也是这样说。可是,这种情况下谁违约了?违约是有过错的,那么谁是过错方?为什么还要给过错方违约方解除权?所以,违约方解除权这个观点,连基本的自圆其说都做不到啊。
从这个角度下就知道,法学界很多人多年来养成的碎片化的思维而造成的后果。这些人的观点总是顾前不顾后,在一个小点上自圆其说,造成很多麻烦。比如《民法典》第580条,本来是要帮助当事人从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得到解脱,并清理相关财产返还问题。可是,我国法学界提出违约方解除权之后,这个问题反而无法正常解决了。因为违约就要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责任怎么承担呢?
另外,面临新的生活,以后还要学会解释法律,还要运用《民法典》。比如关于无形财产和数据财产的问题,《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承认数据资产和无形资产是中国最重要的财产。数据财产论文发表了很多,不能说是汗牛充栋,也能装五六车了。书写了很多,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国家社科基金设立课题,对此花钱不少,但是这一方面值得肯定的成果很少见。我看了这几年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我认为,一些研究成果脱离了民法的基本原理,其结论就没有多少实践价值。依据民法基本原理,一个财产能够用来交换,那么它必须具有特定性或者确定性。数据资产怎么能叫做资产?一个方面是从侵权的角度去考虑,另外一个方面,现在要培育数据市场,数据市场就是说数据可以交换,数据如果没有确定性,怎么去交换?无论如何,数据应该像物权一样基本上固定化,而且还要有一个交易转移的明确标志或者表征。比如说,我把这个数据资产交给赵先生,那么怎么能交到赵先生的手里?这个事情得要有一个技术上的手段和法律上的手续,交出去我就没有了,而且要确确实实地让赵先生取得。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律技术方面的道理,很多学者都不讲,他们只讲数据市场很重要等等。如果不讲民法原理,这些道理就不能算作法理。
再进一步细节的分析交易的过程中间,刚才我提到的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问题。最近我在努力推动《不动产登记法》的立法工作。该法毫无争议是我们国家国计民生中间的基本法律。不动产物权是国计民生的基本权利,它包括了两部分立法,一部分就是关于不动产实体权利的立法,像不动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等等,这些就是不动产实体权利的立法。这些立法,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现实需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但是,还有一个法律是《不动产登记法》,它主要解决不动产物权如何表征的法律程序性问题。这个问题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非交易的状态下,这个权利到底是由谁来享有?因为物权是抽象的,所以需要在法律上予以表征,说明这个权利归属于谁。这就是不动产登记发挥第一个作用。这就是静态表征,就是通过不动产登记,通过登记发证。还有一个方面的表征,就是动态交易过程中的表征。比如,我要把这个房子卖给赵先生,我们俩订了合同以后,要交付房屋,但是房屋的所有权怎么转到赵先生的手里?就是交付房屋,然后通过登记过后的方式来表征所有权的变动。不动产权利的这个表征,在民法上称之为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抵押权也是这样的,转移所有权也是这样的,设立用益物权,设立担保物权等,都是遵循这个方式和原则。
现在我国,不动产登记法还没有制定出来。近年来我在全国人大的一个工作,就是推进不动产登记法。我认为这是属于国家基础性的法律。国务院2014年制定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也是依据我提的立法建议制定出来的。不过我带领的课题组写的立法建议稿原来有60多个条文,结果条例才30多个条文。而且这个条例叫暂行条例。一个法律十年来一直暂行,很不合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暂行条例的立法目的,是要解决不动产摸清家底的问题,土地、房屋、森林、草原、水流、矿藏等,不动产的这些家底是什么,要把它摸清楚,做一个登记,方便行政管理。而我说的,不动产登记是要做权利的表征。这是我跟自然资源部、司法部在这个立法上的不同之处。
在摸清家底这个思路下,很多人就接受了登记确权这个观念,认为登记是不动产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来源,不登记就没有权利,登记了才有权利。这就是学术界被某些老师所称为的主流观点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看法。比如说订立合同来转让所有权,最典型的是买卖房屋,首先订立合同,通过登记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债权意义的合同加上行政法意义上的